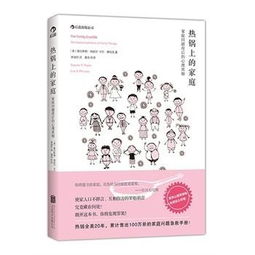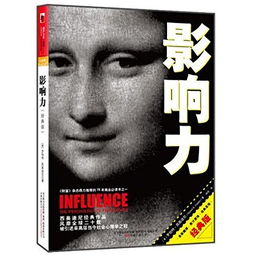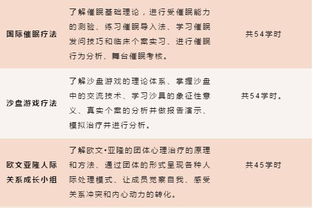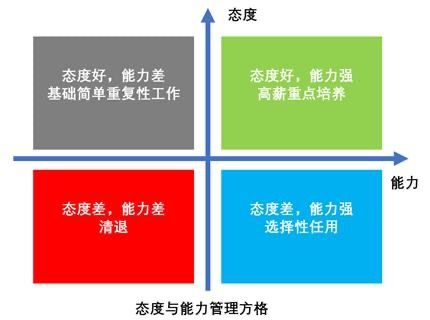《不正义的多重面孔》,[美]朱迪丝·N.施克莱著,钱一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233页,40.00元在正义理论的巅峰年代思考不正义施克莱的学术研究一向反潮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在西方学界甚嚣尘上。施克莱独辟蹊径,以意识形态专家的身份写了一本“法学书”,不仅嘲讽哈耶克,点破法哲学中的世纪争论“哈特-富勒之争”只是同个屋檐下的小打小闹,还超越这些法学个案,作了一项极具洞察力的时代诊断:以法治为代表的去道德化、去政治化话语,只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冷战语境下西方的特定意识形态反应。1981年,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出版,美德伦理学复兴浪潮走向顶峰。施克莱依然不走寻常路,写了《平常的恶》这样一本怎么看都不像政治理论的政治理论著作,从恶习性入手来思考自由主义社会的公民品格问题。

《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也是一本反潮流之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独步学林,社群主义思潮也如日中天。社群主义基本靠批判罗尔斯起家,因此也免不了把正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主题。除了查尔斯·泰勒,其他几位社群主义巨匠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名字里都带着正义:桑德尔的“出道即巅峰”之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沃尔泽致力于将正义“化一为多”的《正义诸领域》,以及麦金太尔那本名字被套用滥了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1986年,施克莱在一本名家荟萃的文集上发表长文《不正义、伤害与不平等:一个导论》,引来时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圭多·卡拉布雷西的讲座邀请。施克莱于1988年作了斯托尔斯法理学讲座,这是耶鲁法学院最古老也是最富盛名的讲座,本杰明·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罗斯科·庞德的《法哲学导论》以及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等法理学名作都源自斯托尔斯讲座讲稿。《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便是以这次讲座为基础,吸收了昆廷·斯金纳、斯坦利·霍夫曼以及沃尔泽等人的意见后修改而成的。
《正义与平等——此时此地》施克莱绝不是简单在罗尔斯和社群主义者之间选边站。相反,她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标签下进行批判。她认为,一直存在一种思考正义的主流模式,它以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为典范,绵延两千年,直至当代的罗尔斯与沃尔泽。她将这种思考模式称为“常规正义模式”,认为其低估了不正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她把自己归入以柏拉图、奥古斯丁和蒙田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传统,致力于揭示主流正义理论的傲慢无知。书名“不正义的多重面孔”想要表达的便是,常规模式对不正义的理解太过简单,必须以一种“更直接、更深入、更关注细节”的方式,重启对不正义现象的思考。
朱迪丝·N. 施克莱,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历任美国政治学与法哲学协会主席、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图为1966年《哈佛年鉴》所刊施克莱照片。区分不幸与不正义“在什么时候,一场灾难只是一件不幸之事,什么时候它是不正义之事?”施克莱以这样一个问句开启了全书的讨论。
按一般看法,答案显而易见:“如果这一可怕事件是由外在的自然力量导致的,那它就是不幸之事,我们必须忍受自己的苦难。假若它是居心不良的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超自然的存在者——引发的,则它属于不正义之事,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慨与怒火。”这种普通人略加思索就会得出的观点可被称为“起因模式”,它根据灾难的起因是自然事件还是社会事件来区分不幸与不正义。
“起因模式”显然是个非常粗陋的答案,施克莱对它的批评大致可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自然不一定必然,相反,许多自然灾害是事先可防、事后可控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已经可以准确预报。即便是地震这类尚难及时预测的灾难,也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来减轻其灾害程度。此外她也提到,文化或者说社会因素不见得完全人为可控,但对此并未多作展开。因此,自然和人为的区分并没有太大意义。科技的发展打破了“自然”与“必然”之间的牢固关联,社会科学的进步则让我们看到了,人难以彻底走出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的控制力也许比自然更强。
这个问题还与意识形态立场相关。鼓吹小政府的经济学家大概会把大量源于政府不作为的灾难界定为不幸。因为按他们的看法,政府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承担这样那样的义务。
“起因模式”仅仅将行动者直接施加的伤害看作不正义,因此会把大量不正义行为界定为不幸,进而引发消极不正义现象。
消极不正义是施克莱浓墨重彩渲染的一个概念,是她在“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中最关注的一个面孔。什么是消极不正义呢?它区别于积极主动施加的伤害,表现为面对他人的苦难,站在一边什么都不做。消极不正义者往往会诉诸必然性话语,表示“这也没什么办法”“这就是生活”,非常心安理得。真的“没什么办法”吗?施克莱不这么认为。她在书中专门用了一节篇幅检讨各种必然性话语,特别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
施克莱把消极不正义概念追溯至西塞罗,后者的相关讨论发生在罗马共和国的语境中。施克莱承接西塞罗的思考,将消极不正义限定为一种“公民观念”,亦即将其视作公民品质的缺陷,而非某种普遍的人性恶。因此和许多道德概念不同,不是随便哪个人都会遭受“消极不正义”指控。它专门适用于那些生活在比较理想的社会之中的公民。这道理也不难理解:在某些社会,人们时刻生活于恐惧之中,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站出来帮助别人;不同流合污积极施加伤害就算不错了。简言之,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站出来为自己的公民同伴主持公道、排忧解难的“道德成本”不同。理想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便是,不会让人频繁陷入道德困境,能够比较轻松地做一个好人。
施克莱这本书谈的主要是美国。就消极不正义而言,施克莱认为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在发生灾难后,热衷于追责/甩锅,忽视善后工作。这一指控可能仅适用于美国等少数国家。在其他国家,防止消极不正义的关键也许恰恰是积极批评追责。
三个模式
拜施克莱有意追求的松散文风所赐,此书没能明确区分“起因模式”和“常规正义模式”。根据其论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两者的区别:“起因模式”基于未经深入反思的常识观念,给出了区分不幸与不正义的一组具体标准,“常规正义模式”则是思考正义/不正义问题的一般方式、标准步骤。许多人对具体的区分标准可能看法不同,但他们的思考都遵循这一模式。因此可以认为,“起因模式”只是“常规模式”的一个具体版本。
“常规模式”是如何思考正义/不正义的呢?它专注于正义,认为不正义只是正义的缺席。按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论述,正义的核心表现是遵守规则,特别是法律规则,以确保每个人获得、保有其应享份额。罗尔斯说得透彻:“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显然预先假定了什么是应属于谁的,什么是他应得的份额的解释。”简言之,“常规模式” 预设了应得观念。所谓正义,就是在假定现有规则符合合理应得观念的前提下坚守规则,违背规则即不正义。
除了“起因模式”,我们还可以从施克莱的散乱论述中提炼出“常规模式”的另一特殊版本,将其命名为“共识模式”。“共识模式”用社会共识来为规则奠基,主张某些规则体现了“我们”——特定历史文化共同体成员——最深刻的信念,因此是“我们”真正认同也真正可取的。“共识模式”的有效运作因此依赖于社会的高度同质性:在“谁应得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上,整个社会拥有共识,虽然可能是有待诠释的共识。
施克莱在书中着重批判了自己的亲密好友沃尔泽的共识观,认为所谓共识,只是社群主义理论家在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引导下,通过随意解释社会成员的想法创造出来的幻象。相比各路乍看高深莫测的理论,施克莱的批评平白直接,但却极具力度:
民族精神的先知式化身或传统主义化身领悟到了共享意义的诸种意涵,他们从不会拿这些意涵去和实际存在的看法——尤其最不利者和遭受恐吓者的看法——进行比对。将共有文化与和谐一致的政治利益相混淆只是一种障眼法。通常来说,文化共享的是语言,除了表达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敢于表达的话,语言还可以使我们表达对彼此的厌恶和鄙视以及不正义感。如果处于社会中最不利地位的成员无法清晰、自由地说明他们的感受,那么我们应该假定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哪怕他们——就像许多黑奴那样——又笑又唱显得心满意足。
《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顺便一提,施克莱还对罗尔斯作过类似批评。众所周知,罗尔斯的前期理论有较为明显的普遍主义色彩,后期理论则限缩为一种地方性辩护方案,即在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语境下,力图说服观念各异的人们接受同一套稀薄的政治正义观念。可以不太严谨地说,罗尔斯的后期理论是在提炼宗教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道德经验。在一封写给罗尔斯的信中,施克莱指出,罗尔斯的后期理论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这样的社会中存在价值共识。她认为,罗尔斯需要给出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这一任务无比艰巨。施克莱总是对共识的虚假性、压迫性格外敏感,哪怕是具有自由主义属性的共识。常规模式的问题及施克莱的开放性方案
“常规模式”有鲜明的司法化特征,其基本逻辑可以这样拆解:公认的规则规定谁对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于是相关主体有了义务,有了正当期待: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所谓不正义,便是不该做的做了,或该做的没做。据此,受害人的主观感受并不重要,正如在司法审判中当事人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规则和事实。
问题是,谁来制定规则?谁来判定规则是否被违反了?
施克莱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她认为,在多元社会坚持要找到“一套”规则体系是不可取的。她说,“……我们还是那么无知且多样,不适合任何单一的规范体系”,“昨日坚如磐石之规则如今只显得愚顽”。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主流规则体系带有压迫性和欺骗性。所谓的正确规则,往往只是符合强者利益的规则,是对强凌弱的意识形态包装。施克莱引用了蒙田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当女人拒绝这些世上通行的生活规则时,绝不该去责备她们,因为是男人在未经她们同意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些规则。”因此,按施克莱的看法,常规模式不仅无法消解不正义感,还会否认不正义感的存在,乃至否认其正当性,进而助长消极不正义。
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承认,有一些主流规则体系,特别是已经被历史淘汰的规则体系,确实带有压迫性和欺骗性。但问题是,一切规则体系都如此吗?多大程度上如此呢?诚然,无论适用何种规则体系,都会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受害者”的不正义感会不会只是一种无根无据的主观感受,是遇事习惯抱怨者的无聊牢骚?
约翰·密尔便认为,不正义感只是一种情绪反应,在未经仔细考察之前不能判定其道德属性。而在尼采眼里,不正义感更是一种“群畜的怨恨”,完全不足挂齿。
施克莱以“不是民主思想家,轻视没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庸俗的历史神话”等大而化之的评判,轻易打发了密尔和尼采对不正义感的质疑。她几乎是不加论证地认可了她眼中“民主理论最伟大的代表”卢梭的立场。卢梭认为,受害者的不正义感“内在、自然地就是准确的”。施克莱虽然要比卢梭节制一些,没有天真地相信心怀不正义感的人必然占理,但她愿意推定这一点,优先听取受害者的声音。她写道:
如果说民主确有道德含义的话,那就是下面这些:民主意味着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很重要,意味着他们的权利感必须被认可。最不济每个人也都得有表达观点的机会,公民们感知自己所在社会中的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平之事的方式不能被忽视。
积极聆听受害者的声音是一个涉及民主原则的大问题。民主的价值根基是平等尊严观念,这一观念使普通人的不正义感觉变得敏锐、不正义感受变得重要。而在等级制时代,被压迫者相对“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其不正义感既没那么容易被触发,也不会被严肃对待——在“统治阶级”思想家眼中,这虽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政治风险,但并没有道德层面的重要性。
和施克莱的其他作品一样,《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也是一本没有明确结论的书。施克莱并未给出自己的标准,来区分不幸与不正义,她说:“我的目的不是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因为本书的论点就是,我们无法在一般层面或者说抽象层面划出这样一条分界线。”这和她对常规模式的批评相一致。施克莱对常规模式的批评绝不是“既有的一切区分标准都有问题,真正可靠的标准尚待探索”,她的观点比这彻底得多:任何试图一劳永逸找出区分标准的做法都是误入歧途的,它们都不恰当地忽视了不正义感。

施克莱拒绝给出区分不幸和不正义的精确标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她打算给出什么样的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
施克莱高度肯定法治,认为相比个人复仇,法治是一种进步,可以更可靠地实现正义。这道理也不难理解:许多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报复,报复行为往往会陷入癫狂。但法治毕竟是常规模式的最大典型,它的基本逻辑就是依据既定的抽象规则,来安抚在具体多样、无法预料的个人经历中产生的不正义感。因此,它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心中的不正义感和报复欲。
施克莱主张,“不仅要根据现行规则公平对待一切不正义感的表达,还要以更好的、可能更为平等的规则为目标,来聆听不正义感的声音”。这引出了民主政治。法治必须辅以民主,才能较为妥当地减轻人们心目中的不正义感。
在民主政治中,人们可以有效表达自己的不正义感,不正义的规则于是有机会被改变。不同群体在政治论坛上相互竞争,彼此有输有赢。因此,通过持续的民主过程,个人心中的不正义感与法治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有效调和。
总之,施克莱关注的不是给出结论,而是不要轻易下结论。保持开放的政治空间,让愤懑委屈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她心目中应对不正义感的最佳方式。
怀疑主义与政治理论的未完成性
前面讲到,施克莱对常规模式的批评能否成立,关键要看如何评价受害者的不正义感,特别是,这是否可能只是一种无根无据的抱怨?在这一问题上,她几乎是不加论证地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卢梭式的民主立场,怀疑哲学,信赖大众。那么施克莱如何能说服那些对民主不抱同情的读者呢?他们大概只会觉得这种圣母心态肤浅且天真。我们可以联系施克莱的怀疑主义立场,努力帮她填补这一论证空白。
虽然对亚里士多德、罗尔斯这样的大思想家,施克莱也免不了说几句客气话,但她显然认为,常规模式是误入歧途的。原因在于,这一模式缺乏怀疑主义精神,对人的能力过分乐观。
施克莱追随蒙田的怀疑主义精神,认为之所以不可能找到终局性的规则体系,归根到底是因为人在认知和心理层面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认知局限性即是客观上的认知能力欠缺,心理局限性则呈现为种种心理弱点:容易被个例引导;面对不利信息不愿改变自己的看法;惯于用内在动机解释他人行为,用外在因素为自己开脱……这些心理弱点最终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判断。
这里需要区分下常规模式的发明者和生活在常规模式下的人,施克莱同时怀疑这两类人的认知和心理能力。施克莱说,“常规正义模式也许完全无可非议,问题只是,它不适合我们。它并无错谬之处,只是在实践中行不通、靠不住,因为它所预设的心理和智识品质我们并不具备”。这话怀疑的自然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她似乎并不怀疑理论家能给出一套尽善尽美的正义观念,问题只是,它脱离了现实。不过所谓“脱离现实的尽善尽美”本身就是个无足轻重且含糊不清的概念,我们不如绕过施克莱的修辞性表述,直接认定她对理论家构造常规正义模式的能力抱有深刻怀疑。
但施克莱绝不是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相反,在根本问题上,她的观点无比坚定:视残忍为首恶,认为人最恐惧的莫过于恐惧本身;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让人摆脱残忍和恐惧,自主且不受偏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过对于体系化政治方案,她总是充满怀疑。她认为,由于认知和心理层面的缺陷,我们对世界、对他人的内心乃至对自己总是缺乏足够的了解。特别是,理论家总是容易低估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经历感受的复杂性。这种无知的自信不仅会导致那些抽象系统的理论脱离现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家往往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从而走向危险的改天换地式乌托邦信念。因此,施克莱的怀疑主义是一种以非常具体、非常克制的认知和心理怀疑主义为基础的政治怀疑主义,怀疑各种体系化政治观念,怀疑学者、官员相较于普通人的认知优越性。相应地,她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骨感自由主义,没有远大抱负,仅致力于守护自由,捍卫多元性,宽容边缘群体。
施克莱格外着迷于人心的复杂性。她把对人的动机、情感和欲求的探索称为道德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绝没什么科学主义色彩,相反,它是非常人文化的。施克莱主要借助各种小说戏剧、社会事件来体察、展现人心的复杂性。她并不觉得人心有多么玄奥离奇,一直拒斥那种脱离文本、脱离语境、凿之过深的解读。但她确实认为,理解人心是再难不过的事情。最大的障碍是经验的匮乏,即没见识过、难以想象、难以理解一些人物类型、情理逻辑、习俗规矩。
施克莱将道德心理学视为政治理论的核心,而道德心理学远不够完备。她说:
社会说明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心理学。除非我们真的知道社会主体的动机是什么,否则我们不可能完全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知道的就只是心理学。关键是群体而非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但如果没有科学上恰当的心理学,就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正如朗西曼所知,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心理学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道德心理学远不够完备,因此,政治理论也要保持一种未完成状态。这种“心理学现实主义”是她拒斥体系化理论的最大原因。重视不正义感、拒绝给出区分不幸与不正义的终局性标准是她的这一立场在不正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她时常将自己这种侧重道德心理学的政治理论路数区别于热衷体系化、抽象化的哲学路数,后者在她看来就是一些“为了避免矛盾和例外,为了超越前哲学形态而设计出来的论证和反驳”。
确实,很多理论乍看系统严密,但细究之下,不过是作者带入一大堆未经反思的预设,借助自己非常有限、非常单调的生活塑造的零散直觉,在非常技术化地处理问题,犹如沙滩上建大厦。正是因为意识不到自己的经验、自己所依赖的理论脉络的有限性,看不到无法被套入学院理论条条框框的生活现象、人心感受,这种系统精密的分析才得以展开。以这种方式得出来的系统化理论,面对实际生活自然毫无说服力:它本就缺乏对生活的理解力。热衷于这类研究风格的学者普遍不读文学、不关心历史和其他各类经验研究,在人际交往中呆板拘谨,听不懂玩笑接不住梗,和施克莱确确实实是两类人。《平常的恶》《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与分析风格的伦理学、政治哲学著作也确确实实是两类书。它们立足于历史经验、日常生活,选择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捕捉那些“逃离了理性化”,但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又无比重要的现象。
《平常的恶》与施克莱风格最相似的当代名家大概要数伯纳德·威廉斯。威廉斯终生关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认为现代道德哲学一直在逃避真实的道德生活,无法应对其复杂性特别是悲剧性;体系化的道德理论不仅注定失败,还会歪曲我们对伦理生活的理解。施克莱的思想主题也可以被非常贴切地概括为“政治理论与哲学的限度”。她着迷于社会生活的“单纯表面”,警惕体系化理论,拒绝透过现象看到所谓的本质,喜欢通过讲故事来帮助读者找回对政治道德经验的感受力。但施克莱似乎过分轻易地拒绝了体系化努力。体系化有助于暴露我们思想中的不融贯、不一致处,逼迫我们头脑中的各种观念相互碰撞缠斗,从而使我们想得更为细密周全。确实有不少哲学家狭隘无知,缺乏感受力,热衷于自欺式的理性化。但也有足够多的哲学家务实而诚恳,努力将我们的零散直觉以一种尽可能清晰系统的方式梳理出来,从而深化、细化我们那些模模糊糊的观念和感受。拒绝体系化只能是诚实面对具体现象的体系化努力失败后得出的结论,而不应成为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便已设定好的思想姿态。否则,它很容易变成抗拒艰苦思想劳作的漂亮说辞。仅就我阅读施克莱的体会而言,很多问题她完全应该想得更系统、更精确一些。
具体到不正义这个问题,硬要给出一套终局性的判断标准确实是荒谬的。但除了给出标准并接受批评、不断修正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像施克莱那样停留于空泛的思想史点评和零散的个例解读吗?开放的政治空间确实很重要,但这个空间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能够让不同的标准、让抽象的标准和具体的感受相互对话,彼此修正,从而不断提升其合理性。如果不能具体指出现实生活的复杂肌理在哪一点上挑战了某套规则体系,那么我们必须说,这种以“复杂/具体”为名的批评本身却是空疏抽象的。相比空洞地告诫理论家“不要傲慢”,更重要的也许是具体分析那些傲慢的理论到底错在哪里。否则,这种告诫姿态只会体现出告诫者本人的傲慢乃至无知。
顺着这一话题,我们还可以谈谈《不正义的多重面孔》颇受诟病的一项主张。
施克莱的一些论述暗示,把不正义理解为正义的缺席是错误的,应该抛开正义,独立地研究不正义。例如她说:“它们视下述观点为理所当然:不正义只是正义的缺席,一旦明白了何为正义,我们就会了解所需了解的一切。不过,这一信念也许并不正确。如果只盯着正义,我们会错失许多东西。”她主张,应该“直接将我们眼中的不正义经验视作独立现象”。
问题在于,不正义就是“不”正义,不正义即正义的缺席,这是一个概念真理。将不正义视作独立于正义的现象显然是荒谬的,深入思考不正义本身就意味着反思既有的正义观,两者在概念上必然关联。因此如果咬文嚼字的话,我们只能说,独立于正义来理解不正义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关键在于,要摆脱追求普遍性与确定性、拒绝矛盾和例外的哲学认知模式,转而关注具体的、个人化的受害者视角。因此,施克莱真正想要打破的思想桎梏并非正义本身,而是对正义的一种哲学化认识模式,即她所说的常规正义模式。之所以要“独立于正义”,仅仅是因为一谈正义便容易陷入常规正义模式。总之,从不正义入手仅仅是策略性的,方便我们调换视角,从抽象思维转换成更贴近具体经验的思想焦距。
对这个小问题的分析既展现了施克莱的反体系化、反哲学立场,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施克莱对精确严密的思考方式可能偏见过深。至少对她而言,这种思考方式并不会构成什么“认识论障碍”,没有这种思考习惯才是她许多问题的根源。
《不正义的多重面孔》的四种读法
《不正义的多重面孔》是一本典型的施克莱作品。它不作精确的概念分析,没有严密的谋篇布局,显得非常松散,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这是她有意追求的蒙田式随笔风格。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作品是难以分析的。它只有模糊的总体立场和诸多零散的闪光点,很难概括出明确的论点、论据、论证结构。
因此,在努力做出体系化分析后,我们还得尝试捕捉那些被遗漏的侧面,尽量还原这本书的多重面孔。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梳理它和施克莱其他著作之间丝丝缕缕的思想关联。
这本书是施克莱的晚年著作,和《平常的恶》《美国公民身份》同属一个研究序列:美国政治思想研究。我们可以先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这本书。

《平常的恶》探讨了美国社会中寻常可见的五种恶习性。但为什么是五种而非四种或三种恶呢?为什么是这五种而非另外五种恶呢?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施克莱并未给出明确说法。她似乎就是顺着蒙田的一句话想到了这样一些恶习性。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不正义特别是消极不正义算作第六种平常的恶。
“美国公民身份”原文是American Citizenship。在施克莱的论述中,citizenship的含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民身份,另一类是公民品质,主要关注公民能否做出符合公民身份的行为,是否尽了公民义务。我们可以说,施克莱晚年的两本小书都是在谈American Citizenship,这本谈美国公民品质,那本谈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公民身份》第二种读法是把这本书和《守法主义》放到一起,将其看作“永恒少数派的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母题在不同理论语境下的具体演绎。和《守法主义》一样,这本书也有极强的法学色彩,连批判对象——守法主义和常规正义模式——也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是同一种思维模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中的具体呈现。它们的主题都是反对以法治话语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规则本位思维模式,后者意味着不再关注实质争议,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按既有规则处理。施克莱虽然高度认可法治乃至形式主义思维的实践价值,但反复强调其局限性,努力让湮没于主流规则体系之下的少数派声音、让实质争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学者给施克莱这种独特的自由主义立场贴上了竞争性自由主义的标签。
《守法主义》《不正义的多重面孔》时不时会讨论必然性话语,反对宿命论观念。这又把我们引向了施克莱的第一本著作:《乌托邦之后》。这本书细致描绘了启蒙时代的政治乐观主义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败。启蒙哲人和十九世纪的宏大理论家有一点非常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结构性因素,对理性的力量、对人的能动性充满信心。这也许是施克莱想要找回的政治观念,一种反宿命论的政治观念。施克莱政治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可能是最稀薄的,但正因如此,它对政治的期许也是最大的。最后,这本书显然有极强的卢梭色彩,免不了让人想起她那本大名鼎鼎的《人与公民:卢梭社会理论研究》。施克莱认为,不正义感是卢梭政治理论的论证主线。对于卢梭给出的方案,她没有照单全收:那太斯巴达了,不可能在现代社会实现。但她青睐的依然是一种卢梭式的方案,一种适合美国国情的民主政治。
《人与公民:卢梭社会理论研究》话说回来,最适合这本书的读法也许就是不刻意追求什么读法,拿起来读,读不下去便放下。施克莱更接近博雅文人而非现代学者。追求干货的专业读者读她的书也许会感到失望,甚至觉得名不副实。她的作品本质上都是蒙田式的散文集,而非现代学术工业制品,分析论证也非她所长。一门心思提炼干货的读者只会错失书中最有价值的那些闲笔,那些脱离论证主线的枝枝蔓蔓。施克莱总是能写出那种洞察世事人心的句子,照亮荫蔽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微妙感受,而读者不断加深的阅世经验也会在不经意间点亮书中那些原本一扫而过的句子。因此,读这种书很考验缘分,需要和生活相互印证才能读出味道,才能慢慢凝结为我们的智慧和教养。这是老派的书,能长进人心里去的书。
免责声明:本平台仅供信息发布交流之途,请谨慎判断信息真伪。如遇虚假诈骗信息,请立即举报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