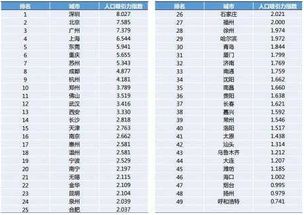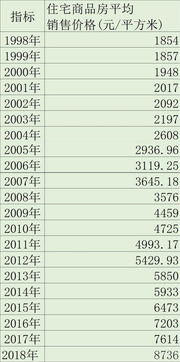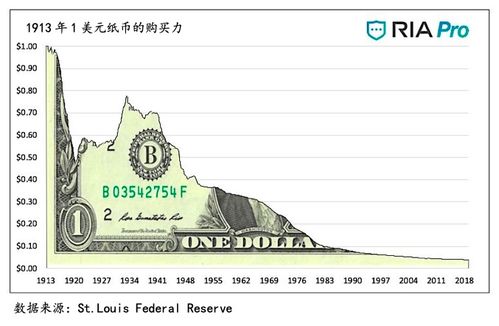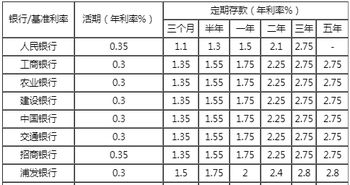“当年拍《银蛇谋杀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交道口电影院拍的,当时电影院被改成了一个家具仓库,把座位都拆掉了,我们没有动那些家具,就在放映室里拍。”
在今年4月,李少红在网上看到有影城倒闭,影厅的沙发座被放到马路边上的照片时,眼泪哗啦一下流了下来。她想起1988年拍摄自己处女作时的场景,那时中国还没有几家电影院,电影的拍摄也全靠国影厂的投资。

此后三十余年,中国电影迎来市场化改革,作为一项产业蓬勃生长,但如今随着疫情的反复,恍惚间竟又有几分和当年相似。
不变的是,不论在怎样的产业环境下,总有带着电影梦的新人踏入这条河流,总有人还在拍摄或等待拍摄自己的处女作。
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正是如今中国新人导演的重要一站。走到第七年的青葱计划,首度举办了影展,将过去7届中5部已经在院线公映的影片进行展映,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青葱计划发起人的李少红认为,这是给所有一直以来关注青葱计划的朋友的一个汇报。
从2015年到现在,青葱计划发轫于国内创投活动蛮荒时期,从执行模式上给许多后来者以借鉴。在如今众多面向市场的创投活动中,青葱更注重从电影文本的角度给新人导演以评价和培养,并在作品面世之前给予全流程上的帮扶,以期为行业做好新兴人才储备。
青葱计划自身也在不断进化。过去六年里,拿到国家扶持金的历届五强学员已有30人,其中6部影片已经在院线公映,3部影片在网络公映,另有11部影片已经拍摄完成,正处于在后期、审查或等待放映的进程中。手握这样一本成绩单,让青葱有足够的储备影片可以筹办影展,并且在未来每一年将影展像“滚雪球”一样稳定地举办下去。
在行业因外部环境不断反复的当下,市场是否还有意愿和余力去扶持新人导演成为了一个迷思,而走到第七年的青葱计划穿越电影行业的发展周期,证明不确定性中仍有确定。
青葱成为青葱
2016年初,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算过这样一笔帐:中国电影行业一年大概有300部影片上院线,如果以每年平均拍一部影片的高效率来工作,一年就需要300个相对成熟的导演。但根据王长田的观察,整个行业里市场大概能用的导演差不多只有100个左右,还有大概200个导演的缺口。
同样出于对“200个导演”缺口的忧虑,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前一年决定办一个扶持新导演的计划,取名青葱计划。
在青葱之前,国内的创投活动并不多,李少红也曾参与其中。彼时的创投让学员对着李少红等导演前辈讲演,由导演来打分,但最终决定投资的却是场外的投资人,她感觉根本逻辑是错位的,“如果讲演的目标是钱,那就应该冲着投资人讲。让我来打分,难道我打分高了投资人就一定会投钱吗?这个关系就不顺。”
而彼时国外的创投活动,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青年导演们先在主办方处登记自己的项目信息,然后投资人对哪个项目感兴趣,就去找人单独约谈。方向上没错,但具体流程上太“大浪淘沙”,效率有限。
于是青葱计划决定集各家所长,先由学员在舞台上反复讲演,让投资人对项目有所了解之后,再进行单独的约谈,“没想到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全国的创投都开始按这个办法做了。”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打样作用,但和之后兴起的其他电影创投活动的差异在于,青葱计划的培养目标,不完全是为市场提供人才。
市场和职业的诉求是略有不同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道出了其中微妙的差别,“我们去扶植培养这个青年导演,其实目标不是简单的说给一个商业洪流当中加一些生产力。我们希望导演能够多一个责任,多一个担当,尤其是用年轻人的方式,用新一代导演的语言,去记录时代记录人的这样一份责任。”
“记录时代记录人”,可能恰恰是当下电影行业尚且紧缺的价值。作为本届青葱计划影展的开幕影片,2005年由李少红导演、周迅主演的电影《生死劫》,就是这样一部记录时代的电影。其改编自真实故事,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爱与恨。导演管虎在观影结束后也提到,电影在作者性和商业性之外,有时还应该具备像《生死劫》一样的社会提醒功能或社会记录功能。
能注意到电影在作者性和商业性之外的价值,得益于青葱计划的属性,“因为青葱计划是导演协会主办的,所以我们不是站在市场或者上帝视角来评判学员,而是更注重电影本身的文本,作为过来人,教学员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文本,以及一些成为导演所应该必备的技能。”李少红表示。
不只是创投,青葱计划也是一个针对新人导演培养的长期计划,会关注新人处女作从筹备到诞生的每一个环节。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刘仪伟用这样的比喻来诠释青葱和市场上其它创投活动的关系:“其它创投能够让你通过你的作品浮出水面,但浮出水面以后,是继续漂在水上还是再沉下去就管不了了;而青葱计划是陪伴,浮出水面之后陪你一直成为一艘小舟,慢慢的成一艘船,所有的导演协会的成熟导演都会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
“但陪伴不是替代”,李少红强调,“我们不会去替他们拿主意,不会替他们拍。我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认清要拍什么,怎么才能够拍出来。”
长成的青葱们
所谓“陪伴”,究竟如何达成,或许“青葱们”自身更有说服力。

在第三届青葱计划学员、《日光之下》导演梁鸣看来,青葱计划对新人导演最重要的训练之一,是提前熟悉生产一部电影的所有正规流程,“当时拍了两支短片,拍的过程中让我们自己去担任制片人的角色,自己去报预算,把各种发票都做好。相当于在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逼着你去按照最正规的流程去完成你那么小的一个短片。”
这些更贴近产业的内容,是从各大电影学院毕业的新人导演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李少红看来,电影学院教的是基础,青葱不教基础,而是做学员们成为导演的最后一站,“就是临门一脚的那一站。”
除此之外,梁鸣还提及,青葱计划孵化的作品,选择什么样的制片团队、发行公司,包括到底是走艺术院线还是做传统发行,青葱计划都会给到相应的建议,帮忙把关。
第一届青葱计划学员、《兔子暴力》导演申瑜同样提到,青葱计划在影片送审阶段和宣发阶段都有提供帮助,“当时龙标还没下来的时候,少红导演一直在帮着询问;到了放映的时候,青葱也在自己的平台上给了很多的宣传,我们当时因为疫情也没有首映式,只有一个小小的发布会,少红导演也去了。”
尽管《兔子暴力》是青葱计划目前已公映作品中票房最高的一部,但在申瑜看来,青葱计划对于她的帮助不仅在于单片的落地,更来自于对个人导演品牌的输出,“在做活动的时候青葱一直会把我们带着,其实是在保持我们的一个曝光率,让我们一直能被业内和公众看到。”
“像保姆一样”,是青葱的气质,但也并非始终如此。七年走下来,关于新人导演的培养方式,青葱自己也在总结经验教训。
据李少红所述,最早的时候,青葱认为不能过多地干预导演的项目,而是只扮演类似“婚姻介绍所”的角色,“你们俩想在一块相个亲,我们可以提供场所,至于你们俩谈的成功不成功,会不会登记结婚,我们觉得好像应该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但走过最初几年,她发现,这和“相亲”还不太一样,因为相亲没结婚介绍者没有责任,但青葱计划是有责任的,要将政府的扶持金落实到位,要让每年选出来的这些片子真真正正地拍出来。
除了项目要落实之外,对新人导演的培养也需要付之以更多的耐心。前几年青葱将重心放在晋级上,未能晋级的导演将会被淘汰。这个过程中,拼的是导演的悟性和提高能力,也就导致了很多作品其实没有打磨到位,成熟度不足。
自去年开始,青葱计划开始了名为“深耕精作”的2.0阶段,将入围人数从30强减少到了20强,但这20个项目会跳过讲评环节,直接进入系统学习过程。这样的变化能给新人导演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训练得更久,把一些真正有潜力的项目打造得更完善和成熟。
“改变了规则之后,我发现有些创投的短片拍得真好,连我都傻眼了,所以我们就又去找钱,给他们补拍的机会,把一个短片打磨到最好为止,而不是说拍了一个之后,又再去拍一个新的,那样的话提高反而不明显。”李少红感慨道。
什么市场都需要新人导演
在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导演贾樟柯提到了产业环境和新人培养之间的关系,“以前经济好的时候,企业还能拿出一些钱来,大家都会有一份公益心,不出于商业考虑去投资一些年轻导演,所以年轻导演的机会还是有的。现在经济一收缩,闲钱少了,机会就没了。”
这也是电影人的共识,在本届青葱计划影展的开幕论坛上,第七届青葱计划主席黄建新提到,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里,“商业电影对艺术电影的帮助不确定能有多大,但是艺术电影对商业电影未来的帮助一直很大。大家一直想把中国电影的市场做到很高,是因为电影有了盈利,文艺片才会有人投。如果电影都亏,文艺片除了以前的国企投没有人投。”
在青葱计划初创的头几年里,市场发展势头迅猛,年度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银幕数也与日俱增涨破八万块。在那几年,青葱计划因为场地所限,时常面临现场投资者“站都站不下”的火爆场面。
疫情之后,电影市场遭受打击。在今年这低迷的半年里,让青葱也感到意外的是,来参加的投资方格外得多,且青葱面向的还都是有过电影投资经验的专业投资人。李少红表示,“当时我特别担心报名,现在哪有人还投年轻人的片子,我特别不乐观,结果没想到火的不行。”
“火”的一方面原因是今年开放了线上参与的渠道,给了无法亲临北京的投资人以机会。另一方面,在李少红看来,这说明投资者对行业的信心仍在,“这个行业不是说会一直持续这样子的低潮,严冬还是会过去的,所以大家还是会希望有一些项目储备。”
即便行业的情况再艰难,在从国营电影制片厂投拍电影时代走过来的李少红看来,如今的新人导演也有太多的选择。
1993年,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各制片厂必须自负盈亏之后,电影导演们突然没有钱拍戏了。“当时一下子觉得自由了,但是走到北影厂门口站在大街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钱在哪儿呢?去什么地方找钱一点概念都没有。”到如今,尽管行业盈利困难,但导演筹拍电影也都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融资渠道。
从拍摄选择上来说亦是如此。在李少红看来,过去的老导演们只有胶片一种选择。而对如今的新导演们来说,如果院线电影项目暂且没法成行,也还有网络电影、网剧、甚至短视频可供选择,“不管大小,我的心态一直是只要让我拍我就干。对导演这一行来说,手不拍就生了,创作这种东西一定要保持一个状态,长时间不拍以后,感受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世殊事异,李少红也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方式,成长于这个时代的年轻创作者们,有着属于自己考量。
在过往的从业经历中,李少红观察到,如今的青年影人更聚焦于自我,重视个人感受的,而上一代影人是没有个人体验感,重视社会观察性的。
梁鸣导演的《日光之下》讲述的是一对兄妹的故事,影片集中从妹妹的视角出发,诠释她的个人感受和在家庭关系中的存在感。而作为该片监制的李少红更多地会对故事背景中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感兴趣,“我觉得那个部分拍得特别好,但他最后没有要。我很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这就能看出来两代人都是拍社会题材,关注的焦点和角度却是不太一样的。”
在黄建新眼中,新人导演的新思维和新视角,反过来也是老一代导演需要去丰富和拓展的,“你的经验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使它变得丰富,这才是意义。因此青葱计划是互动的,不单单是培养了年轻人,也反过来推动了我们上一代导演的进步,推动了导演协会所有成员的这样一个进步。”
养一棚大葱需要120天,而养一群“青葱”,导演协会已经花了7年。这7年,是在交互中成长的7年,也是见证了电影行业高低起伏的7年,青葱计划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确定性。
免责声明:本平台仅供信息发布交流之途,请谨慎判断信息真伪。如遇虚假诈骗信息,请立即举报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