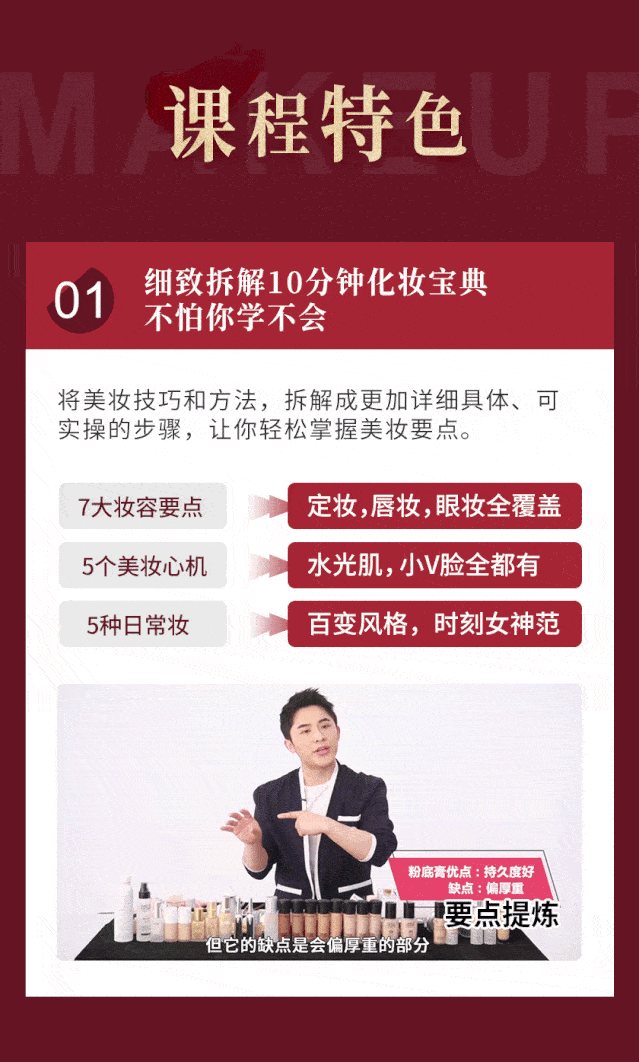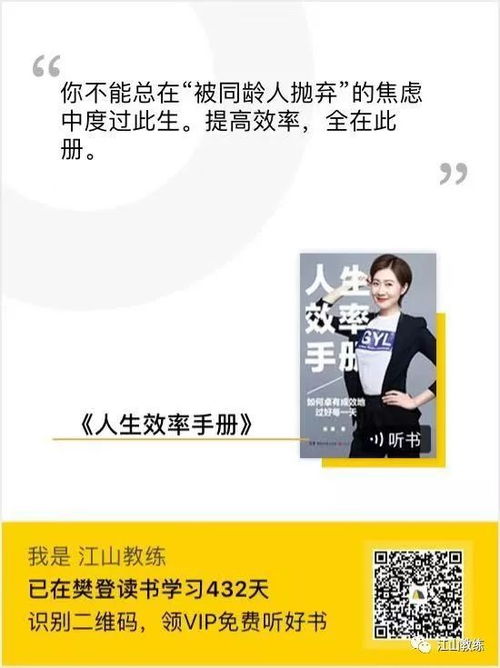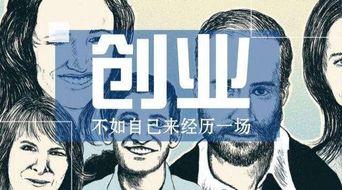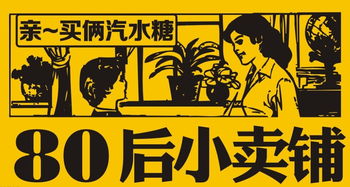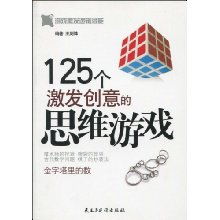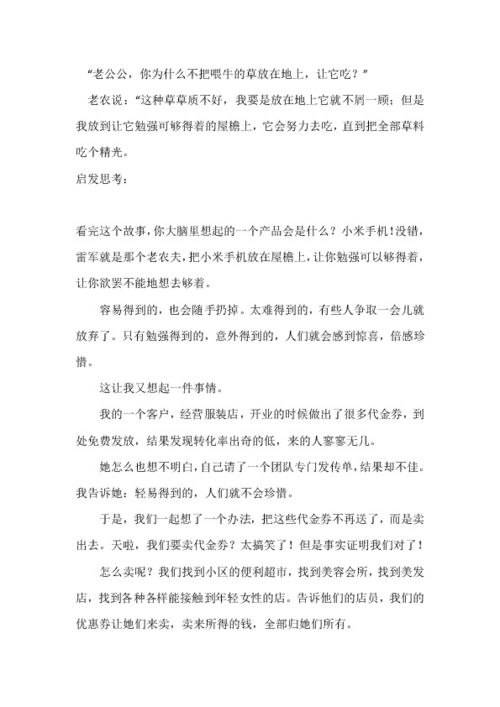本文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姚,

转载请联系授权。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坐飞机。窗明几净的机场,臃肿嘈杂汗流浃背的火车站,温柔微笑的空姐姐和冷峻凶狠的乘务员,还有书香书屋里印着的卡内基百科全书、松下幸之助的《人生智慧》和后来的穷爸爸富爸爸,还有憨厚大叔大声呼喊的《法制日报》,构成了旅途中天堂与地狱的区别。
常见的机场和站台读数。
曾经,“法制日报”的功能被“热搜”和“微博”取代,书籍在高铁平台上卖,在机场也卖。卡耐基和松下幸之助,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马云的《未来已经来临》和乔布斯的自传不再是唯一一部放在显要位置的作品。我们知道世界是不同的。虽然我们有一些钱,我们可以乘坐飞机,享受更舒适的铁路站台,但我们毕竟不富裕。
李开复和马云的书也是近年来的畅销书。
阅读材料的变化到底反映了什么?
2012年,《创客:新工业革命》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2013年,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引爆了当年的电影市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事件,其实并非毫无关联。如果你在中国最大的学术论文网站上搜索“创客”一词,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发现:2012年,全文中出现“创客”一词的文章大约有40篇,而2018年,这类文章已经膨胀到2000多篇。这说明“创客”的出现不是简单的名词转换,而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那么,在“创客”诞生之前,是哪些术语主导了我们自我管理的逻辑,这个逻辑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人生变化,这就不得不提我们小时候占领机场的高端商务人士必须随身携带的读物,都属于一种知识:“成功学”。
古今转换
从“成就”和“美德”到成功新概念的诞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功”二字并不是指一个人的成就,一般是指效果的显现和目标的达成。如《尚书·龚宇》中:“于Xi玄贵,你成功了。”特别是治水目标的实现;《盐铁论》中“黄帝战成功,唐舞伐孝”专指黄帝战胜蚩尤。总的来说,在宋代以前,“成功”是一个中性的褒义词。在《左传》中,“立功、立言、立德”成为士君子不朽的三大支柱。道家虽然强调心平气和,无为而治,但也强调只有成功了,不靠现有的成就活着,才能保住某人自己的价值和名号,也就是所谓的“成则昌,亡则不去”。很明显,道家的冷漠不是讨厌“成功”,而是讨厌“邀功”。
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新兴的理学知识分子逐渐把道德与功利的区别上升到完全对立的地步,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夏商周时期以“尊德”为主,后世只注重“政绩”的理想政治。这时,“成功”已经不等于完成了某项事业。它强调以个人利益和成就为最高目标的经营活动。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仍然局限于帝王将相的政治商业,与后世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商业大相径庭。南宋著名思想家为了功过,与朱打了无数场笔墨官司,谁也没有说服谁。但由于理学在南宋末年成为官方学问,且与明代科举结合紧密,所以中国学者只要是在承平时期,都不敢谈“成功”。虽然他们谈论的是“道德生活”,但目标是当代人眼中的成功:房地产、地位或对他人的统治。
不同版本的《铁血王者——卡内基自传》。
晚清时期,这种“德”与“成”的对立主导了中国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发展近代工业经济的争论。洋务运动时期,保守的伍仁是理学家。他反对军民工业西化的原因是道德高于成就。但是,在洋务派和后来的维新派的士绅中,为了解决近代工业的资金来源,商业活动的合法性仍然是一个道德上棘手的问题。所以“成功”的问题受制于保家卫国的政治前提,成为开工厂开银行的正当理由。直到清末,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些与当代成功学相关的人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905年,工业杂志发表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青年训练》。通过编辑卡内基选集,它强调了年轻实业家的工业成功与他们个人品质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从卡耐基名言的编撰开始,中国资产阶级实业家开始将成功视为以个体企业家为中心的目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企业家精神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们发现《做事》中选取的演讲有两个特点:一是企业家人格的理想化和英雄化,这的确是西方资产阶级“成功”价值观的基础。但为了让文章更贴近中国读者,卡耐基的“企业家英雄”被刻意塑造成一个“读他国文学”的学者形象,给当时大多由士绅转变为民族资本家的中国企业家增添了亲切感。更有甚者,作者将卡耐基对自己作为苏格兰移民的母国勇敢性格的研究整理成册,刻意将卡耐基的理想企业家打扮成勇士、勇者,无形中为中国企业家引入了“商场如战场”的游戏隐喻。其次,卡耐基强调企业家必须忍受挫折,意志坚强,这显然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吃苦”的说法,即“天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骨”。而被后世视为“成功学”核心问题的自我催眠法和人际逻辑的灌输,在这本汇编中却完全没有出现。这也说明,作为19世纪西方企业文化中的“成功”价值观,它并没有深入渗透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土壤中。
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对“成功”的系统论述。但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成功”观念,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深入人心。卡耐基的故事和言论在报刊杂志上被广泛看到,并被系统介绍。1941年的《上海生活》杂志上,出现了卡内基的详细传记:《钢铁之王——卡内基传》。这本传记不仅强调了卡内基的致富之道:勤俭持家,勤俭持家,还强调了他作为一个富人独特的财富观。钱是身外之物,在社会上使用才是正道。这样的卡内基形象,完全符合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眼中一个具有“新教伦理”的企业家形象。这篇文章的发表,暗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中“德”与“成”的对立,开始受到现代西方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基于个人而非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成功案例也受到大众欢迎。1917年创刊的《成功人士传》,试图通过刊登古今中外先贤的“成功”案例,激发国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本杂志的成功案例大多是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功德”案例,显然是针对传统儒家社会重道德轻功德的政治氛围。但也有草根阶层成功致富的案例,如《商场决战的邱传》、《赤手空拳取得巨大成功的传》。这个强调机缘、机遇、人品结合的普通商人的成功故事,自然为小本经营却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新市民阶层提供了榜样。

当代“成功研究”
借助集体策略,个人主义得以实现。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强调物质激励和绩效控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将厂长负责制引入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体系,重新将企业家的个人成就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等同起来。但此时,企业的“成功”,国家的富强,现代化仍然息息相关。
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这个全新的“赢家”。从表面上看,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成功人士似乎是一个“经济人”,其目标是企业利益最大化。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完成企业改革,增加利润的“政治人”。此时,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竞争对手不是市场规则和竞争对手,而是缺乏现代技术和集体凝聚力松懈;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细微的成本核算和准确的市场定位,而是在企业中重构微观秩序和引入新技术、新手段的最终决策。
新星
作者:柯云路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制度的全面引入,“成功学”的春天才到来。原因是一大批个体私营企业家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们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相对于繁杂的数据报表和经济金融知识,成功企业家的典型故事成了他们了解现代企业制度最清晰、最生动的入门书。此时,早已被遗忘的卡内基重新获得了一股复兴的热潮,紧接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巴菲特等一系列科研机构,或者私人“成功研究所”写出了成功的作品。90年代,在严肃文坛声名狼藉的柯云路,试图走通俗、畅销文学之路。他还写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情商》,并在作品还未加工时就将当时流行的成功术语“情商”应用于其中。他延续了80年代的老调,在书的开头就谈到了“个人的成功”和“民族的成功未来”的关系。这种本土化的“成功学”尝试,是为了让他重新成为“成功作家”。然而,这种“成功学”将成功学的问题从企业管理领域推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能否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提高社会地位,是区分“成功人士”与“不成功人士”的重要标准。
根据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将市场视为一种通过交换实现财富成分均衡分配的制度,而前者则将市场视为一种赢家通吃的准军事游戏。“成功学”的兴起表明,在90年代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已经从一种资源配置的逻辑,转变为一种人们不得不无意服从的“思想-行为”的装置。大多数国外版和本土版的《成功学》都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商场和职场是战场,被“胜利/失败”的二元逻辑所主导;其次,每个人都必须有策略地改造自己的行为,完成一些精神上的修炼,才能赢得职场和商场。最后,在事业/职场成功的过程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非常重要。那些无法融入集体和团队的人,必然会遭遇失败,而不是成功。
这个“成功”的逻辑包含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核心。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从个人主义人生观塑造自我行动的“自我技术”教科书;但是,再往深里说,这种个人主义只有借助集体行为策略才能实现:要有“情商”,“团队精神”,即使有创造性思维,也要有效说服团队,等等。这说明成功学的流行是新自由主义文化意识的扭曲呈现。那些成功的读者,在思想上似乎接受了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然而,尚未消失的单位制和私企、外企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使得通往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既“正能量”又“令人心痛”的情绪劳动。正所谓“世间万物皆有学问,一个人的感情也是有学问的。”一大批中文系作家出了《西游记》《红楼成功学》,也卖得很好,更“通透”的读者干脆重读曾国藩、李宗吾的《传统中国成功学》。
新的成功故事
“创客”来了,“成功学”不再成功。
曾几何时,成功学的作品不再成为都市白领的床头读物,而成为“10元三本”的街头读物。新一代的成功故事,不再写那些日本老爷爷,而是开始关注电影里打败台湾、中国、台湾顶尖武打明星的那个曾经的大学英语老师,或者另一个大学英语老师,他的人生故事最后变成了另一部电影。这个转折点显然与社会的另一个转折点有关。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创客”与互联网革命有关。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早期互联网企业英雄的故事,就会发现“创客”、“创业”等词汇在中国的泛滥,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而是与现代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微机普及和早期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弄潮儿的创业故事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次包含了一个独特的工业产品的诞生。不管这个成品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一些真实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管理的故事。一方面,比尔·盖茨除了文化潮流的变化,和巴菲特、卡内基、艾柯卡没什么区别。这只是一个企业英雄利用各种人际关系登上巅峰却不失初心的故事。
“创客”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首先,创客不创造“真实”的东西。他只是利用互联网创造的“去人格化”的人际关系来组装东西。所以,创客卖的不是东西,而是互联网营销链条上的节点。其次,创客的成功不是靠单纯的智力和技术,也不是靠传统人际关系中的情绪劳动,而是洞察力和偶然性的结合。
根据创业故事改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
在这样的“创客”概念背后,是一种全新的市场和社会组织原理。《创客》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认为,由于跨区域的物流和互联网的信息流,许多为特定客户群体定制的“小众”产品也能在全球范围内找到足够多的用户群体,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甚至蚕食那些只关注客户需求、采取大规模生产策略的大公司。与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相比,按照胜负逻辑组织市场和社会的原则。表面上看,“创客”的盈利方式已经转向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求-供给”导向的市场原则。一场激动人心的创业之旅似乎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通过一个独特的应用软件,一个带有独特流行文化标志的“文清”手袋,一套图案独特的手工茶点,甚至一个搞笑的视频,只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市场,就能找到不需要自身修养或社会关系就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手段。似乎胜败逻辑不再适用于我们。只要找到合适的思路和机会,每个人都是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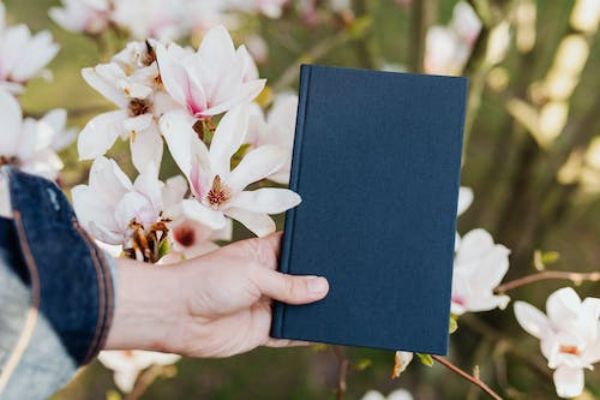
这样的“创客”故事,让新一代成功企业的励志故事取代传统企业家的英雄业绩,成为机场和高铁读者的新宠。世界变了,但我们变富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读者也不知道“创客”的兴起必然代表着新自由主义市场配置危机的加剧,而不是这一危机的解决。
与成功叙事不同,创业叙事的核心不在于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和社会关系管理,而在于“个性”。“个性”不仅仅是指创业者独特的个性,还表现在创业过程中如何抓住市场趋势,找到独特市场份额的“卖点”。但在具体的市场运作中,“个性”的制造并不是企业家的洞察力,而是依赖于基于逐利本能对市场的刻意筛选,而现代工业高强度的再生产能力使得每一次筛选都不可避免地将个性变成共性。潮中“创客”的快感,在这一轮筛选-复制中迅速转化为挫败感。他们不会成为第二个“马云爸爸”,而是当下市场潮流中朝不保夕的创业劳动者。然而,在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劳动边际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时代,大量无法进入组织化企业的白领不再拥有追求成功的主动权。他们被抛入“创业”的大潮中,靠着“个性化”的产品,梦想着既有钱又自由,从未预见到被资本大潮碾压的危机时刻。
此时的创业传奇,不再是他们可以模仿的英雄故事,像成功故事一样,而是努力过程中难以捉摸的安慰。
本文为寻找中国创客原创。
未经授权的复制是不允许的。
免责声明:本平台仅供信息发布交流之途,请谨慎判断信息真伪。如遇虚假诈骗信息,请立即举报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