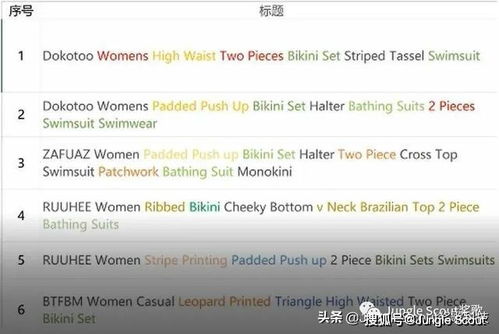作者就是那个人。
崔,女,1939年7月出生于香港。1958年9月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中学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当过农业工人、养鸡员、副排长。之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当生产队农技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研究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6号,1990年获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省农垦名录。1990年至1992年编辑撰写了50万字的《红兴隆科学研究所学报》,1993年获黑龙江省地方志优秀奖。1993年获得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及成果”荣誉证书和徽章。

第三,父亲去世的风波
1961年冬天,我从农场管理二部调到农业部后不久,二哥用了四封电报告诉父亲,他快死了,催我回北京。我对瘫痪在床多年,能走路却不出去工作的父亲非常反感,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解放后的新中国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那时候我正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像保罗对他父亲说的:“保罗残疾了,还想为国家做贡献。与其过着没有工作的寄生生活,不如去死。“如果这次不是学校让我回家,如果不是收到第四封电报,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回去。老公陪我走,半夜到家,知道爸爸已经死了六天了,几个小时后就要下葬。我妈对我说:“打开棺材,看看你爸!我给你留着棺材。”我说,“不要看。”母亲悲伤地说,“你父亲去世前,一直睁着眼睛找你。他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词。港、港、港的人打电话找你。我告诉他你很快就会回来。等等!但是他根本没有等。你为什么不能见他?”我还是说,“别看了!“棺材必须被钉上。
这是1961年12月。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姚大哥。
这是我大哥在1962年5月寄给我的,也是为了改造我父亲去世后,我对如何认识我们家的想法。

一辆敞篷卡车在呼啸的北风中呼啸而过,把我父亲的灵柩和我们一家人一路拉到了北京第三人民公墓。没有墓碑、花圈、烧纸和贡品;没有请和尚念经;没有披着白布的戴孝,但每个人的左臂上都缠着黑纱,脚上穿着一双用白布缝制的棉鞋。下葬前,我妈说:“大家跪下,给你爸磕头!”两个孩子拿着铲子在坑边等着,我老公和我姐夫。我们八个孩子站三排,我和大哥站最后一排。前面两排都跪下了,只有我和我大哥没跪。我问我大哥怎么办。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下跪。我不在乎你做什么。”我觉得我是共青团员,不能下跪。我不会做资产阶级的孝子孙儿。可是,妈妈的眼神冷冷的盯着我,我动摇了。我一条腿跪下,准备跪第二条腿的时候,前两排的兄弟姐妹已经磕头完毕,开始站起来,我也跟着。当棺材慢慢掉进事先挖好的、已经渗了一尺深的水的沙坑里时,我妈大声哭道:“我没有火化你,我把你埋在水里了。”我知道她同时也在责怪我,因为我问她为什么不火化。
第二天,所有的邻居都说我们做的太简单了,我们家连一张我父亲的画像都没挂。他似乎从未拍过一张照片。大哥说:“邻居的指责其实是对我们的赞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心里得到一些安慰。“然而,我那爱恨分明的婆婆,在收到我们的信后,突然从天津来到我家。她指着我丈夫,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说:“你在这里玩什么?谁会是你孝顺的儿子和孙子?他们是黑的,我们家是红的,你不知道!你真是气死我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空打了一个霹雳。第一次觉得问题严重了。
老公还说了些我们家“黑”他们家“红”的话。我妈听到了,她一直记得,直到1996年底我老公病逝。我妈去天津看过他几次,我也不想让我80岁的白发妈妈去送她62岁的黑发儿子,因为她十年前就已经送走了我老公52岁的二哥。当我办完所有丧事回北京给我妈看遗像的时候,她泪流满面地说:“我就想问问他,我们家怎么黑了?”他们家是怎么红的?”我无语了。
我看着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钟表、大玻璃柜等值钱的东西卖掉;为了谋生,两个弟弟,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正在用电光纸和稻草杆做小风车。他们放学回来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让妈妈把他们卖掉换钱买第二天的学习用品。14岁的妹妹在城外的乡下上街捡煤渣挖野菜,让我心痛。而且,据说父亲还因为吃野菜导致胃穿孔。记得解放前几年,姐姐和表姐因为我们穷,经常拿着旧衣服在街上摆地摊,求路人买我们的衣服。有一次,我上学迟到了,因为我在卖东西。我被老师打了三次,还因为不能按时交学费被学校开除。那种生活太可怕了。为什么弟弟妹妹年纪轻轻就要过这么艰难的生活?他们正在长大,正在上小学,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条件。我姐姐应该帮他们一把。
说实话,我没去过穷人家,没见过黄世仁,没被穆仁之打过,不知道穷人家有多惨。只是在我的高中同学中,我觉得我很穷。我经常不能按时支付学校每月八元的伙食费,但学校不让我住校。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我每天都要带饭,来回路上要骑将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我同宿舍的很多同学都戴着手表,经常花钱买一个叫“东方红”的三色奶糖。有一次他们给了我一块,我舍不得吃。我养了好几天,终于吃到嘴里了。味道很好。我抵挡不住诱惑。我悄悄拿了一毛钱去买。交钱的时候才知道是17分钱一张。我狼狈地退出了商店。他们经常课后去看电影,比如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那时候电影票是两毛五,一个三角。我真的很想去看他们,但是我没有钱。因为怕别人笑话我穷,每当同学问我要不要去看电影,我总是找理由不去。以后我会努力争取到中苏友好协会文化中心举办的音乐鉴赏会或文学讲座的免费门票,每次见面后免费看一场苏联原版电影。直到那个每次去要票都给我的男人,在我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那个男人说:“太晚了。让我给你送行。”在电车上,他把手搭在我肩上,我吓得再也不敢走了。
如今,食品价格上涨了。甚至在穷乡僻壤的北大荒上大学的时候,一顿饭就一大勺冻白菜汤和萝卜汤,偶尔还能吃到土豆片汤。每月的伙食费是13美元50美分,更不用说北京了!妈妈哭着说:“这里哪个没有人均20块钱,又吵又不够花!我能用这些钱做什么?”
1950年和1953年,母亲生了两个弟弟,家庭人口增加,父亲常年生病。我家原来住在大方家胡同的那个大院子,早在1957年就已经卖掉了,我买下了北新桥附近的那个小院子,用这笔钱养活自己。后来钱花的差不多了。当时家里要靠未婚的二哥当工人挣钱,维持家庭生活,供四个弟弟妹妹读书。二哥和珂瑶同岁。我,一个妹妹,结婚一年了,但是二哥为了养家,不敢结婚。大姐没上高中就结婚了;表哥没敢上高中,考了一个免学费的教师进修学校,去了乍得青年农场;懂事的大姐初中毕业后不敢上高中,就去了免学费的护理学校。我二姐还在上初中;父亲病重,住院和手术欠了医院几百块钱。此外,他还欠了棺材和埋葬费。我为弟弟妹妹们的理解和进步而高兴,为家里的彻底没落和艰难而难过。随着我妈一起哭,我老公拿出八十块钱递给我妈。
回到学校,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接受了一些学校教材的刻印任务。我终于凑够了十块钱,寄给了弟弟妹妹们。信中说:“晚上不要做风车,多读书。”没想到,这杯水车薪让我老公知道了。他说:“你牺牲了休息时间去帮助那个家庭。你的位置在哪里?感情上,你和资产阶级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不迷茫。”他还说:“你看,我给了我婆婆八十块钱,我觉得很开心,好像给了你面子,但是后来我大哥批评我,我根本就不该给那钱。害怕弟弟妹妹受苦,你是什么感受?他们的困难只是比过去更严重。他们是富裕家庭的成员。他们怎么能和北京的生活费比呢,北京的人均月生活费只有8块钱。要知道,剥削阶级的孩子要替父母背黑锅,要过苦日子。他们还在吃‘固定利率’。那不是剥削是什么?”
说到“固定利率”,我还真不知道。我从来不问家里每个月有多少钱,二哥挣多少钱。父亲病逝几天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张75元的汇款单,我收到了。当时我看到的汇款单是75元。我很惊讶的问我妈是谁送的钱。我妈说是山西发的“定率”。我说应该按月发还是按季度发?可能因为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头脑太混乱了。她说:“每个月,不,每个季度。”我老公说:“你看资产阶级。是这样的。全家还在出轨。你不是今天才知道‘固定利率’吗?不要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说实话!”但是不要说没人认钱的时候,现在有几个孩子,有多少收入?父母收入多少?还有其他收入吗?收入如何?再说一遍,多少钱?但是老公认可我,我却无法反驳。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出身”好的孩子不了解家庭情况,那就是无产阶级父母不想让孩子分担家里的困难。我老公在1953年“整肃革命党”的时候被审查,因为他妈没告诉他他是怎么辛辛苦苦攒钱买那两个半房子的。但是,“出身”不好的孩子,不知道家里的情况。肯定是资产阶级父母故意隐瞒家里的剥削,故意不让孩子知道。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太明白“定息”剥削的含义。四十多年后,我终于看到了“股票”、“收款凭证”和一封信,是1966年我大哥去山西插队时,他母亲送给他的;“收款凭证”是山西那个每季度代收款的人给我弟弟的。不知道哥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在山西十五年,他把这些东西连同行李一起带回了北京。也许把这些东西送到历史博物馆更合适。那张“股票”印得很好,正面写着:“股东崔中原,出资额为人民币6,818.85元整。”背面写着“此股年利率定为5%。这只股票的利息将从1957年1月开始,每季度支付一次,金额为85元23分。”我妈是家庭主妇,没学过。她不知道这只股票会持续多少年,会不会一直付息。文革期间,她托别人给山西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现在是‘兴而不灭资’的全国文革运动。我们意识到这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一件大好事,就是真心拥护政府的英明指示,是时候改变过去‘资本家’的生活了。因此,我将最初投资于贵公司的‘股份’寄给您,请查收。向革命致敬。崔中原的爱人宋于震1966年8月22日送的。”
《收款凭证簿》记载了1957年7月至1966年7月每月收款金额及经办人印章,前十年共收款3409.43元,占股本的50%。那时候连开小店的所谓小业主都觉得这是剥削,何况是不工作的白领!但我又在想,1956年,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国家采取了“赎买政策”。实际上,十年定息只收回了一半本金,爷爷的6818元血汗钱也没了。也有人说我们“剥削”了。我们剥削了谁?如果这笔钱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呢?不仅有利息还本金,那还叫“剥削”吗?
我妈本来想把股票交给国家,这样她就再也不做资本家了,但是她不知道上交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定息的末期了,那股从此作废。但我戴着“资本家”的帽子,直到1990年12月入党。我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组织告诉我“家庭背景”是“工人”,没有“海外关系”。
我丈夫继续对我评头论足,他说:“认真考虑一下。公公生病去世为什么不火化?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奢华的葬礼?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排场作风吗?我婆婆老了还烫着头,穿着花衣服。这不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什么?姐姐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是什么,不是腐化共产党员的大舅子?你得给你公公跪下……”老公的一系列批评,就像从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一样,砸在我头上,吓得我再也不敢刻钢板给弟弟妹妹们寄钱了。但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更何况穿花里胡哨的衣服烫头发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我们逃到香港住了几年,然后回来在上海和广州住了半年。烫头发穿花衣服是当地人的习惯。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才46岁。为什么他们不能烫头发,穿漂亮的衣服?如果无产阶级烫头发,穿花衣服,怎么解释?
免责声明:本平台仅供信息发布交流之途,请谨慎判断信息真伪。如遇虚假诈骗信息,请立即举报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