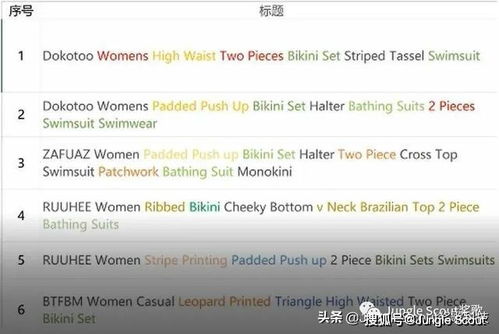今年是金克木诞辰110周年。金克木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印度文化研究者,著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蜗角古今谈》《无文探隐》等。传奇的是,金克木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但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无论在武汉大学还是北京大学都极受学生喜欢,而且博览群书,学贯古今,能掌握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对天文学、数学等自然学科亦有浓厚兴趣。
批评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以时日为序,理出金克木一生线索,取其本人文字,佐以考证、参校所得,撰成一本以自述为主、稽核为辅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这是金克木先生迄今第一本传记、年谱类作品,今年夏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书封。全书作上中下三编,分别名为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作家出版社供图9月3日,“一个传奇和他的本事——《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新书分享会”在杭州举行。黄德海与作家、文学评论家李庆西,作家、《江南》杂志副主编哲贵,作家、资深媒体人萧耳来到解放路购书中心,聊起了一代大家金克木的求学、成长、机缘、情感、晚年生活。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新书分享会“对我来说,金先生最卓越的地方,还不是他在印度和梵文专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是他晚年不断总结和提炼的读书和学习方法。”在黄德海看来,这些方法其实是金先生在现代社会情形下,思考怎么读那些浩如烟海的书。他将金克木的读书方法形容为“剑宗读书法”。《笑傲江湖》里,华山派有气宗和剑宗,气宗是将所有的基础都打好,再开始练高层次的剑术。剑宗则把自己的眼光练得无比锐利,在任何实战里寻找对方的缝隙,然后来决定自己的出剑方式。“所谓‘剑宗读书法’,其实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把什么都准备好才开始读书。我们不得不先知道自己要读哪些书,知道书的整体和结构,然后蹒跚着走进书的世界,一点点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读书方法。”活动前后,黄德海就新作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黄德海 摄影 孙甘露【对话】澎湃新闻:你因什么机缘接触了金克木先生?
黄德海:说起来真是一个长长的故事。1990年代末,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个一间屋的小书店,守店的是一个有些妖冶的老板娘,长长的卷发,鲜红的嘴唇,涂着黑红色的指甲。很多同学去店里,说是逛书店,恐怕为了看老板娘的居多。店里的书,大部分是小报级别的,游走在色情和暴力的边缘,我们进去买这类书,老板娘冷着脸,一脸嫌弃的样子。有一天,我居然在他们乱糟糟的书架上看到一本《末班车》,作者有个五行八卦一样的名字,金克木。我一看目录,书里好像天南海北谈了很多东西,便拎过去请老板娘结账。老板娘拿起书,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完全忘记了她长什么模样了,但那个笑我记得非常清楚,心里认定是她对我的鼓励。带着这一笑的能量,我晚上回去一口气就把这本《末班车》读完了,觉得说出了我的很多想说又不能说出来的话,大受启发。
我读书有个习惯,只要读了一个作者的书,觉得好,就会去搜他全部的作品来读。那时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太丰富,我只找到了几本金先生的作品。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了很长的金克木作品的收集过程。那时候没有孔夫子旧书网,收集到作品需要运气。大约七八年吧,我到上海读书快两年了,才差不多收齐了金先生的书。但很奇怪,当时看到有一本《庄谐新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一次听张汝伦老师讲课,他大谈金先生的杰出。下课了,我忍不住问,张老师是否有《庄谐新集》。张汝伦老师说,金克木先生的书,我全有。那么,嘿嘿,张汝伦老师下周上课的时候就带来了。这本书要到后来有了孔夫子旧书网,我才买到的。
澎湃新闻:近些年你陆续编纂了不少金先生的书,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欣赏金先生的人有,但像你这样执着并付出的人并不多见,你为什么认定金先生是中国文化的一位大师?或者说,他为什么值得你一再阅读,一再亲近?
黄德海: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很想把自己认定的人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比。最早写《书读完了》的前言的时候,我把金先生和陈寅恪、钱锺书一起列为近代的三位大师——那时候大师这个词还不像现在这么泛滥,还拉扯上了德里达。当年德里达上海行,其中的一站在学校里,我发着近四十度的高烧,在开着空调的屋子里只坚持了不到一个小时,没听明白他要讲什么,读他的书也不多,却就敢来拉拉扯扯地造自己的学术封神榜。到现在,其实已经无心跟别人比较了,就是一个这样出色的人,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不就足够了吗?
对我来说,金先生最卓越的地方,还不是他在印度和梵文专业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是他晚年不断总结和提炼的读书和学习方法。这个读书和学习的方法,其实从他的文章名和书名里就能大体意识到,“书读完了”“读书·读人·读物”“读书与‘格式塔’”“读书得间”“无文探隐”,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情形下,怎么读那些浩如烟海的书。我觉得金先生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并足以供我们学习。比如面对众多的书,我们要先有个知识结构,这样才能知道每本书在系统中的位置,然后学着给书“观相”“望气”,一眼而判断某本书可能的价值,然后像福尔摩斯一样,围绕着书试图解决的问题一路跟踪追查,越读越有兴味。这个读书方法,我称为“剑宗读书法”,非常有意思,越琢磨越有味道。这样特殊的读书法,当然值得我一再学习体会。
金克木。本文图文若无特别署名,均由金木婴提供。澎湃新闻:金先生的学历和学术成就在后人看来非常传奇,他在北大任教简历“学历”栏上填的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但他就能做到学贯古今,博通中西。编撰了《金克木编年录》之后,你怎么理解他何以做到如此?他年轻时的哪些学习与读书经验影响深远?黄德海:我们心目中的学习,似乎总有个学校在其中,但其实金先生之前,中国长长的教育史,并没有现在这种完善的学校,很多孩子都是在现在看起来不太正规的环境下开蒙的,所谓“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金先生虽然拥有的学历是小学毕业,其实他入学以前即已能背诵四书及部分五经,小学毕业后还从私塾先生接受了两年传统训练,就是怎样用读书来挣口饭吃的训练。后来还曾进过师范学校预备班,不过后来因为学校解散,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后来在印度,师从宗师级的憍赏弥,也不是正规的学校,而是一对一的类似师傅带徒弟——一个大宗师口传心授,是不是比学校里一个老师带很多学生,要幸福得多?
憍赏弥是传奇人物,出身正统婆罗门,早年学佛,熟读全藏,后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并曾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只是受不了那里的严寒气候,过了一段时间便回国了。憍赏弥跟甘地是好朋友,随甘地住过一段时期,“交流了不少思想。但甘地的住处是政治活动中心,他在那里无法长期住下去。甘地入狱,他便离开。有人为他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盖了一间小屋,布施给他”。这个鹿野苑的小屋,就是金克木从学的地方。后来,大概是因为耆那教的影响,并可能有病在身,憍赏弥决定通过自愿禁食放弃自己的生命。甘地建议他到瓦尔达接受自然疗法,并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听从甘地的建议,搬到印度西部靠近瓦尔达的塞瓦格拉姆去住,每天饮用一勺苦瓜汁。
金克木跟憍赏弥的学习过程,真是近乎传奇。他连续两次去找憍赏弥的时间不对,老人家不让他进门。第三次,“这回我才明白了,临走时把表和他的钟对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这故事真跟张良从学圯上老人一样,金先生自己也说,“适有天竺老居士隐居于此,由‘圯桥三进’谓‘孺子可教’”。我还跟朋友说,张良从学圯上老人的故事,是原型故事,此后的变形是五祖传六祖,再之后的变形是菩提老祖教孙悟空,收尾的就是金克木从学憍赏弥。
除了上面提到的憍赏弥,金克木受过教益的人很多,比如傅斯年,比如邓广铭,他们都对金先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傅斯年把金克木引上了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的路,邓广铭让他有机会见识了现代学术的精彩,憍赏弥传授的则是梵文和对梵文的理解。有时候虽然只是一面之缘,金克木就能抓住其精神核心。跟傅斯年就是这样,金先生大概只见过傅斯年一面,谈了几个小时,然后拿着傅斯年送给他的拉丁文《高卢战记》回去,学会了拉丁文,决心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我觉得这是他学术“预流”的开始,居然只是来自一次谈话。
所以,我们一直说金克木是自学成才,但在某些时候,他会说,“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只是因为他学习的速度太快,我们以为他都是自学的。金先生有一次跟人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

说了这些,我们是不是就差不多意识到了,金克木部分的学习和读书经验?轻车简从,在某个情境中直接找到读书和学习的核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也一直贯穿着他的学习和读书之路。
1946年7月,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澎湃新闻:编年录也有各种,有的偏重人生经历,有的偏重学术进境……你做《金克木编年录》的时候是否也有所偏重?如果有,背后的思路是什么样的?黄德海:这个问题正好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这本《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我注重的就是金先生的读书和学习方式,也就是始终围绕着他的思想成长之路。我个人觉得,自孩童时期到晚年,金先生凡有所写,大部分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我在写的过程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即金先生写自己的孩童时期,并不是简单的回忆儿时,更是对儿时的反思,他后来的思考成果一直贯穿在其中。甚至,我很想说,即便是感情生活,金先生也不是停留在怀念和纠葛上,而是从情感开始思考,有很多对人有益的东西。
比如1936年夏天跟女友游莫愁湖。女友说会划船,可船进了湖,女孩子居然不会。“我……拿起桨来向水里一插,用力向后一划,不料船不向前反而掉头拐弯。我忙又划一下,船又向另一边摆过去。她大叫:‘你怎么划的?’……我怒气冲天,又不甘心示弱,便再也不看她一眼,专业研究划船。连划几下,居然船头在忽左忽右摆来摆去之中也有时前进一步,但转眼又摆回头。我恍然大悟,这船没有舵,桨是兼舵的。我也必须兼差。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明是划水,实是拨船。我有轻有重有左有右作了一些试验之后,船不大摆动,摆动时我也会纠正,船缓缓前进了。”真是动人的小儿女情态,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一个绝妙的学习方法,就是在当下情景中,仔细观察,立刻找出解决方案。这个可以针对每个具体的学习,也贯穿在金先生一生之中。他学外语,需要用了就学会,跟这里的事情,是一个思路。
澎湃新闻:你昨天也特别提到,金先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他其实是一个跟现实无比相关的人,他希望自己所有的学问“能用”。比如同样是教梵文,季羡林先生和金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金先生的梵文是从印度学来的,所以金先生能背很多梵文诗歌,还会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到了晚年,金先生也特别关注学术动态更新,这里好像都有一个“学以致用”的思维在里面?你认为他的“学以致用”和当下功利性学习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黄德海:学以致用一直是中国特别重要的传统,章学诚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就是说,古人没有非要去说一个道理,他说的任何道理,都是针对具体的事而发,或许是因为解决得太出色,或许是因为对很多事的处理有共通性,这才有人记录,有人传播。比如《论语》,很可能是学生们听到了特别动心的话,赶紧记下来才有的,否则怎么会有“子张书诸绅”这样的记录呢?这样的记录,跟人心和人生有关,针对每个可能的具体,或许就是学以致用。有了这样的致用可能,人会越来越开阔,因为真正的事无限繁多。所谓的功利性学习,其实心目中只有自己,为自己的私利而学习,会越来越切断跟开阔的相关性,人可能因此变得狭隘和脆弱,经不起社会风浪具体的吹打。
澎湃新闻:金先生曾自我调侃:“我就是个杂家”。他对各个领域源源不断的好奇和兴趣为人称道,但“杂家”这个词有时会给人一种专业性不够的感觉,类似于“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什么都不是很精通”,也有人因此容易忽略金先生的专业性。但昨天李庆西老师说了,我们对金克木的兴趣不在他的主要学问,不是他的学问不重要,而是他的学问太精深,普通人很难进入。你怎么看待金先生的“杂”和他的学术成就?他的“杂”对你的读书学习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德海:或许可以换个方式来谈这个问题,比如,金先生晚年那些看起来像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算专业还是杂学?如果把这些算成杂学,那比例较他的印度学专业大得太多了,所以金先生好像也没什么重要的样子。可换个方式看,谁定义了学术的标准?教人学会读很多种可能的经典算不算得上专业?如果连当时的基本背景都欠缺,专业的程度怎么说呢?是不是引用了十几种外语,其实废话连篇是学问,而说几句人话就是杂呢?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对概念的判断,而不是概念本身。
对我来说,金先生的专和杂是一体,始终没有离开具体情景中的具体问题。也因此,他的“杂”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原来所谓的学问可以如此开阔,又如此具体。或者我再说一个故事,吴小如先生肯定是古文方面的专家了吧,可“杂家”金先生跟他说的一些话,吴先生也视若拱璧,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一点专和杂之间的关系?
金克木 绘画 李寂荡澎湃新闻:金先生晚年有一个重要的提法——“无文的文化”,这类不文或“无文”的文化常被称为民间文化或下层文化。他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识几个字也只写信记账,不大读书。但讲中国不能把他们忘了。他认为无文的文化其实在更大面积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在分享会上你也说到,金先生晚年的文章很多是为普通人写的,为不做研究的人写的,那么他这个做法是否也和“无文的文化”这一思路有关?黄德海:所谓“无文的文化”,照金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过去大多数不识字的人的文化:“不识字人的文化和识字人的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文化的记录是文字的,但所记的文化是无文字的。文字的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学。无文字的文化也发展自己的文学。有文字的仍然在无文字的包围中。……有文的和无文的语言符号传达文化信息互相交流。上下内外有别,但堵塞隔绝不了。不要通气和要通气形成许多社会情况。现在有新闻媒介,音像都可以由卫星传播到全世界电视屏幕上,视听信息更难阻隔了。在不多年前,没有广播,更早些还没有报纸,信息流通有些比较集中的地方。家庭除外,宫廷、公堂都是有文和无文、上下、官民、雅俗相交会之处。此外还有一些场所为信息交流提供方便。社会由此而血脉流通,生长变化。”
这问题我们转化成现在的情形,考虑电影和电视剧对相对数量较大的人群怎么影响,是不是就可以明白?这个地方是不是雅俗相通的“无文的文化”?如果更大数量的人来思考经典,那是不是说明“无文的文化”在逐渐变成“有文的文化”,这样对社会的发展和空间的开拓是否更有意义?因此,写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的文章,是否根本就是为了变化“无文的文化”?因为单薄的反面还是单薄,极端的反面还是极端,只有具备了开阔的空间,人的活动和心理弹性才多一些。
“金克木三书”澎湃新闻:在你看来,金先生的哪些读书方法和心态在当下尤为珍贵?黄德海:金先生读书方法和心态,最珍贵的部分,就是现在这本书的书名,“读书·读人·读物”。这本书原本可以直接叫“金克木编年录”的,但我实在舍不得这个三读,所以还是坚持用了。哲贵曾经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书最后大家都会称呼为“金克木编年录”,忘记掉主标题。我跟他说,可能再多过些年,“读书·读人·读物”会成为一个鲜明的形象,在另外一个方向超越副标题。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读书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我看见过的书可以说是很多,但读过的书却只能说是很少;连幼年背诵的经书、诗、文之类也不能算是读过,只能说是背过。我是懒人,不会用苦功,什么‘悬梁’‘刺股’说法我都害怕。我一天读不了几个小时的书,倦了就放下。自知是个懒人,疲倦了硬读也读不进去,白费,不如去睡觉或闲聊或游玩。我的记性不好,忘性很大。我担心读的书若字字都记得,头脑会装不下;幸而头脑能过滤,不多久就忘掉不少,忘不掉的就记住了。……读得少,忘得快,不耐烦用苦功,怕苦,总想读书自得其乐;真是不可救药。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讲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做‘读人’。”“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我从那些东西也学了不少。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读书真不易啊!”

读书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物,反过来,读物也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这种读书知世法,破掉了认识的壁垒,书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思维,这样做下来,世界处处连通,知识不再是狭隘的,人心也才能开阔。
澎湃新闻:今天的读书环境、读书氛围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金先生还在世,他可能会怎么读书呢?
黄德海:其实金先生一直在考虑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环境怎么读书的问题。你看,这是他1984年写的,跟现在有什么变化吗?“据说现在书籍正处于革命的前夕。一片指甲大的硅片就可包容几十万字的书,几片光盘就能存储一大部百科全书;说是不这样就应付不了‘信息爆炸’;又说是如同兵马俑似的强者打败病夫而大生产战胜小生产那样,将来知识的强国会胜过知识的弱国,知识密集型的小生产会胜过劳动密集型的大生产。”尽管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书是知识的存储器,若要得知识,书还是要读的”。时移世易,读书方式也要随之变化,“读法不能是老一套了”。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读书呢?除了这里提到的《读书·读人·读物》,再加上一篇《“书读完了”》,一篇《谈读书和“格式塔”》,大体可以了解老先生现代社会情形下的读书法。如果足够聪明,其实都不用去读文章,这三个文章名,已经道出了高明读书法的秘密。
所以,如果金先生还在世,我想他还是会用自己的这个读书法读书,只要根据变化的情景微调即可。这个读书法,或许可以再强调一遍,我称为“剑宗读书法”。读过《笑傲江湖》的人都知道,华山派有气宗和剑宗,气宗就是所有的基础都打好,再开始练高层次的剑术。比如说先练紫霞神功,练到第八层,才能练什么剑法。剑宗的认知完全不同,哪里会有人等到你打好所有的基础,任何实战几乎都是一次未知,只好把自己的眼光练得无比锐利,在任何实战里,发现对方的漏洞,上来就是一剑。不是先设想有基础的剑法,而是在具体里处理自己的所学,这跟传统的教育方式非常不同。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因此所谓的“剑宗读书法”,其实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把什么都准备好才开始读书。我们不得不先知道自己要读哪些书,知道书的整体和结构,然后蹒跚着走进书的世界,一点点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读书方法。
免责声明:本平台仅供信息发布交流之途,请谨慎判断信息真伪。如遇虚假诈骗信息,请立即举报
举报